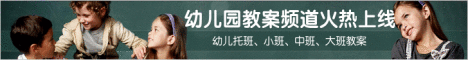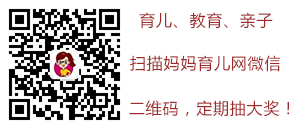徐枣枣今年31岁,两年前,她动起冻卵的心思。外人想象中的阻碍都不存在,父母虽然还不知道女儿为此上了法庭,但母亲早在2017年就主动和她分享过冻卵的新闻。朋友在听说后也都支持这个开庭日没摘鼻钉的姑娘,这是她会做的事。
真正的阻碍在制度。在中国,未婚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包括冻卵在内)不在允许范围内。原国家卫计委2003年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文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直以来,想冻卵的女性都只能选择去海外。
2017年12月,原国家卫计委曾对多名人大代表提交的“呼吁放开对单身女性生育权限制”的建议作出答复,表示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否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调查,加强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冷冻卵子”等技术发展,积极做好可行性研究,审慎推进临床应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单身女性的合法权益。
“这是一个模糊地带,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是当时的规定还在一胎计划生育时代,太陈旧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二胎已经放开、人口老龄化严重,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希望这个案件能提升未婚女性生育需求的能见度,引发更多社会讨论,也把大家的声音传达给相关部门。”于丽颖说。
徐枣枣已经把《建议保障单身女性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权利》的提案和个人建议信寄给了北京的63位人大代表,其中包括小米创始人雷军,目前除了几封拒信,还没有别的回音。
她在意的远超一个“好结果”:被有同样焦虑的女同胞听见、被政策相关方看见、被媒体和他人不偏不倚地讲述。
“关于结果我有心理准备,律师也跟我聊过。案件胜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能被改变,那一定是非常喜人的一件事;要是暂时没有,至少它的影响会存在,会让更多人注意到未婚女性群体的需求,改变一下生育观念,让女性能获得更多身体自主的权利。”
被问到一审败诉怎么办时,徐枣枣直言会上诉,“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努力到最后”。
冻卵技术原本为患癌或其他病症的女性而设。如果癌症或其他病症的治疗方式对卵巢机能有不良影响的话,冻卵疗程就可以帮她们保存生育能力。
慢速冷冻的方式(Slow-freezing)于1980年代面世,成功率并不高。不过,现在使用的玻璃化技术(vitrification)成功率已大大提升。
美国生殖医学会指出,就算是38岁以下、比较年轻的女士,一颗冷冻卵子能够成功孕育婴儿的机率是2到12%。
冻卵需要花费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费用,生理和情绪可能受到不良影响、冻卵的解冻和再次受孕有不低的失败率。庭审中,被告方也提出医院不得不遵守相关部门对单身女性冻卵的限制;技术本身存在不成熟的情况;单身女性生孩子会带来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女性生育年龄可能推迟以及其他伦理争议。
“但是即便如此,也是医院和医生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对当事人进行风险提示,让其自己做决定。单身女性生育权是很连续的事,包括后续解冻、使用,伦理风险等都可以讨论,而不是觉得这件事很麻烦,就一刀切禁止。”于丽颖说。
23日上午,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和律师、哈佛大学法律博士詹青云也联名发文支持,文中指出,中国现行《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中明确提到可以出于“生殖保险”的目的,即男性可以保存精子以备将来的生育,并没有要求已婚身份。一方面允许单身男性冻精,另一方面禁止单身女性冻卵,涉嫌性别歧视,有违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Google、Facebook、Amazon等科技巨头都有资助员工冻卵的政策,携程在去年7月宣布“公司将为中高级女性管理者提供10万元至20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冻卵费用”,这项惯常见于国外互联网大公司的福利落地国内。“多一个选择总是没有坏处。员工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借此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女性员工。”携程CEO孙洁说。